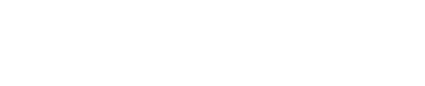历史学院马新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4期发表研究论文《秦汉县域人文地理构造与大一统国家奠基》。

文章认为,秦汉时期的县并非仅是政区范畴,在其成为中央王朝最基本一级政区的同时,也形成了多元复合的人文地理构造。所谓人文地理构造主要指县域政治地理、聚落地理以及社会文化地理的组合机制与结构状态。中国古代县域人文地理构造形成于秦汉,但却是农耕文明出现以来逐步发展演进的结果。自农耕聚落出现,自然地理格局中便有了人文地理要素,人文地理构造开始发生。随着跨聚落区域组织结构聚落群的出现,若干聚落拥有共同的生产生活空间,区域性人文地理构造开始萌生。从仰韶后期到龙山时期,随着城邑出现以及原有聚落群的发展整合,以城邑为中心,附着若干村落的组织结构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期,各方国实际就是相对完整的人文地理组合体,除拥有独立地理空间外,还有稳定的血缘组织结构、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在长期历史传承中,生成了区域性人文地理构造。进入王朝时代后,商周王朝在收纳方国与分封诸侯过程中,并未改变方国原有人文地理格局,而是在前代农耕文明基因传承基础上,实现了更深层次重构,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以封国或封邑为范围的人文地理单元。
文章还认为,秦汉王朝统一后,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若直接沿用西周春秋及其以前的体制模式,则殷鉴不远,难以维持王朝统一与稳定;若彻底否定历史,以军事武力打造一个统一帝国,同样会昙花一现,如西方古代史上一些庞大帝国。所幸的是,秦汉王朝构建起一套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并在这一格局下对历史时期形成的人文地理格局进行塑造,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县域人文地理构造:将县域政治地理延伸到所有地域,保障了大一统王朝建立在完整坚实的地理空间;通过政治地理与聚落地理的嵌合,将行政构造与自然聚落构造有机结合,保障了中央集权政体自上而下直达乡村的统一性;通过社会地理与文化地理的重构,形成县域社会同构与心理文化认同,保障了不同地域民众的王朝与国家认同。
文章提出,秦汉时期的县既是中央王朝最基本的一级政区,又是较为完整的人文地理综合体——县域既是以县廷为中心的区域政治地理单元,又是县城与诸村落相伴生的聚落地理单元,还是相对完整的社会与文化地理单元。这种人文地理格局构造使秦汉王朝实现了与文明起源以来历史的有机衔接,对秦汉大一统王朝巩固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县域人文地理构造的形成对县的稳定性有着重要意义,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标识。此后两千年来,不论政治体制与政区层级如何变化,县始终是最为稳定的存在,在中国古代大一统文明体存续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基石作用。